|
在外封丘人 有深度的解读封丘! 编者按这是9年前刊发在《中国医药导报》的一篇人物报道,文中的主人公当年65岁,今年已经74岁了。我们之所以重新推送这篇报道,主要是感佩于本篇报道的主人公刘杰老先生的人生故事,彰显着我国基层乡村医生“仁心济世”的宝贵精神;而且,刘杰老先生也是我们封丘县唯一一位在人民大会堂做过长篇发言的乡村医生。让我们一起重温老乡医的厚重沧桑的人生履历,一起向为保障千百万农村居民生命健康的乡医们致敬! 年4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由本刊和《中国现代医生》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乡镇医生执业资格问题研讨会”隆重举行。会场内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各界代表及20余家在京及河南的媒体记者。记者获悉,在这些代表者中间,有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乡村医生代表——来自河南省封丘县黄陵镇大山呼村卫生所的刘杰老先生。 据悉,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界代表有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卫生法学会、中国医学科学院及河南省卫生监督所等中央和地方的相关领导及专家学者,作为一名在基层农村工作的乡村医生,年已65岁的刘杰老先生为什么会受到这次研讨会的邀请,并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发言?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随后采访了刚从北京回来的刘杰老先生及其家人。在采访时无意中听到的一句话,破解了其中“奥秘”—— 目睹现实滋生梦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医生是最为稀缺的一种职业。对于那时的农村老百姓来说,生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请不到医生看病。许多人患了小病,就是因为得不到医生的及时诊治而白白丧生。 这样的情景,对于当时刚刚14岁的刘杰来说,几乎成了渗入骨髓的痛苦记忆,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他当时年仅40岁出头的父亲,因患原本不应致命的病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早逝的过程。也就是从那时起,“长大学医,为人治病”的愿望,根深蒂固地埋在了刘杰的心底。 父亲去世后,兄妹5人勉强在母亲的支撑下继续上学读书。渐渐地,承受着生活重压的母亲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身为长子的刘杰,在刚刚考入封丘四中不久后便无奈辍学回家,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 因为忙于生产队的工作,刘杰做一名医生的愿望暂时搁浅了,但他心中“悬壶济世”的梦想一直没有放下。几年后,这个愿望通过一个在外村教学的本家哥哥的引荐得以实现。他被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老中医陈五星收为学徒。陈五星老人沿袭了民间中医带徒学医的那种简单却很有效的方式——让他一本接一本地背诵医学典籍。2年左右的时间,他背熟了《药性赋》、《汤头歌》和《脉诀》等一些枯燥但相当重要的中医典籍。后来刘杰说,那个时候下功夫背诵的这些书籍,终生受益不尽。 转眼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刘杰所在村的大山呼学校急缺教师,当时,有机会做一名教师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面对这样的机遇,尽管学校前前后后派了好几个老师去找刘杰做工作请他到学校任教,但都无功而返。后来,学校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拉上当时的大队支书去做工作,无奈,刘杰只好答应了下来。 谁料他这一干就是7年。这7年中,刘杰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不但继续做着行医救人的梦。他常常是忙完教学工作就把《脉理学》、《中药学》等书籍拿出来琢磨一番。此外,这期间他还自学了西医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开始在村里无偿地为乡亲们诊病行医。 转眼到了1970年,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在毛泽东主席“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因为那时“刘杰会看病”的消息已经在村子里人人皆知了,大队支书便跑到学校去找他和校长商议,调刘杰到村里撑起合作医疗小组的事。因为在那时,各个村都要培养赤脚医生,而培养医生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已经学有所成的刘杰自然成了最佳人选。 刘杰老先生说:“当初硬拉我到学校工作的是支书,后来拉我出来搞合作医疗的还是他。我知道,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当赤脚医生,这是村里父老乡亲们的需要。我很感谢老支书的信任,同时也算是终于圆了我当医生的梦……”但在当时,刘杰已担任了学校的副校长,学校的工作根本离不开他,因此公社抓文教的领导坚决不放刘杰。大队支书一着急,说:“我找俩人换他一个,这总中了吧?”于是,便专门找了两个高中毕业生到学校去顶替刘杰工作。无奈之下,公社领导只好同意了。 “合作医疗”惠泽乡邻到村合作医疗组工作,是刘杰全身心地去做一个好医生的起点。贫寒人家出身、喝家乡井水长大的刘杰,从那时起,就把大半生的光阴,交给了保障乡亲们的健康事业上。 在村大队部的办公房里,有几间专门为办合作医疗而腾出来的房子。平时,刘杰就带着村里选拔出来的9个卫生员在那里坐诊。一个印着醒目的红十字、陪伴刘杰十几年的白色木药箱就是在那个时候置办的。 刘杰说:“还是那个时候的医疗政策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就是要让老百姓都能看上病、看得起病。村民们每人半年上交3角钱的医疗费,就能解决一般常见病的诊治问题。但是,当时一些常用药品的供应问题却很严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医生没有了药,行医看病当然就没有了意义。”面对这种情况,刘杰决定“自力更生”,解决这一实际问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那片广袤的黄河滩地上,很多中草药都可以采集,比如香附、霜桑叶、益母草等。一些难以采集的药物还可以通过老百姓收集,比如鸡内金等药材。采集不到的,就自己种植,比如红花、白菊花等。很快,刘杰这一自给自足的想法得到了村干部和村民们的大力支持。大队还专门给合作医疗组划出2亩地,用来种植中草药。 “医者父母心”。从那以后,刘杰在大山呼全村村民中的口碑越来越好,不仅是在医术上,还有他从那个时候就诞生的“让父老乡亲花最少的钱治病”的行医理念。在此期间,因为大山呼村的合作医疗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刘杰和他的同伴们多次受到县、地区以及省里相关部门的表彰。 1973年,医术、医德皆名闻乡里的刘杰医院(现医院)聘去,坐诊于该院中医门诊室。医院工作的6年,经他看过的病人不计其数。不少人为找他看病未到上班时间就排队等候了。生于贫寒、长于困苦的刘杰感同身受地了解乡亲们求医的艰难,所以,他开处方时就特别注意用最便宜、而且依然有效的药品治病,千方百计地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杰渐渐意识到:在医院给病人看病其实并不比在村里方便。他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应该立即就地抢救的病人等颠簸医院时,已经恶化了,甚至有些还因为这把命搭了进去,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医院坐门诊其实是个错误的决定。 说到这里,刘杰老先生陷入了沉思,而正在干家务事的老伴儿则接着说:“那时候,每个星期天回家,他都会一遍又一遍地擦他那个小药箱,擦完后便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呆呆地望着那个宝贝药箱。刚开始我还说他:‘擦啥呀,你现在又不用。’后来,我也就不说了,我看得出来,他是想重新背着药箱走村串户……” 1979年,刘杰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又回到了村卫生所,继续过起了充实而又忙碌的村医生活…… 淡泊名利博爱四方冬去春来,岁月如水,这么多年来,每天刘杰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大都已是夜幕沉沉。因为一名村医,几乎大多数的病人需要出诊,所以,刘杰的一日三餐很少有规律。渐渐地,因多年来的辛苦奔波再加上吃饭热一顿、凉一顿的,刘杰患了胃溃疡病。这种病夏天疼起来也不是特别严重,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到了冬天,一受凉,胃部就像刀绞,痛不欲生。因为每天忙于四处奔波,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他的胃溃疡一天天加重,最终引发了胃穿孔!不得不医院。 两个多月后,经过保守治疗,他的胃穿孔终于痊愈了,刘杰又开始挎着他的药箱早出晚归。虽说胃穿孔好了,但胃溃疡依然在折磨他。为了给他治病,紧紧巴巴的家已背了近两千元的外债。他很明白家里已没有钱再给他看病了,但为了身体,病不能不治,于是,刘杰开始自己想办法了。他翻书籍、查资料、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一年多之后,刘杰配出了一种中药散剂,竟把自己的顽疾吃好了,且至今30多年过去了,也再未复发过。后来,他又拿着自己配出来的药方试着给别人治疗,结果,凡属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之类的顽症,只需一剂药下来,便彻底根治。这下,刘杰更是声名远播。但是,无论来找他求医的人有多少,他除了把按规定应收的药费如数上交大队外,就只本本分分地拿他一天10分的工分,没提过其他的报酬。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因为大环境变了,合作医疗制度在许多地方都近乎瘫痪,刘杰所在的村卫生所也解散了,心里烦闷的他又医院医院聘去坐中医门诊。其实,刘杰打心眼里不愿意过去,但在当时,一心希望能够维系“治病救人”心愿的他也只有这样。医院轮流坐诊不到两年,医院回了家,并借钱在村里开了个中医诊所——他依然放不下他的那些父老乡亲。 农村医生大都是“全科医生”,中医、西医,外科、内科,甚至妇科、儿科、眼鼻喉科都得兼顾。20多年来,刘杰结合大量的农村临床实践和农村的现实状况,在用中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中风)及妇科病和肠胃病方面,积累了许多可圈可点、切实可行的医疗实践经验。 老百姓的嘴巴就是扬声器。时间久了,大家知道了封丘县黄陵镇大山呼村有一个有名的中医叫刘杰。随之,来他家看病的外乡人也越来越多。有时候,刘杰自己也奇怪,除家乡封丘以外,周围的原阳、延津、长垣及黄河对岸的山东曹县、东明等县的百姓是咋知道自己的呢? 几年前,本村管姓家中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中风引发偏瘫,没有钱治病。儿子不在家,他女儿找到刘杰求诊并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刘杰来到老太太家细心把脉、问诊,给这位老太太开了十几副中药,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前后花费300元左右,就基本上把偏瘫治好了,一个原本躺在床上几乎成了“植物人”的老太太,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了。 “其实,用中草药治疗中风后遗症的病号,大多数都能收到很好的疗效,语言障碍、肢体功能都有明显的改善,最起码能够下床走路了……医院里,光住院费就让这些家境不很宽裕的农村家庭无法承受……”刘杰再一次阐述着他的“让父老乡亲花最少的钱治病”的行医理念。 刘杰说,医为仁术。尽管人们对他的医德医风有口皆碑,但他对名利却看得很淡泊,因为他觉得这没什么,治病救人,本来就是他的职业。刘杰还说:“过去的民间医生讲的是‘穷人看病,富人花钱’,其实这句话对于现在,也有一定的道理。”邻村一个妇女,患了一种很难治的病,医院,花了两万多元,大夫都异口同声劝她回家“想吃啥吃啥吧!”万念俱灰之际,在亲戚的介绍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刘杰。刘杰给她用了一个多月的中药后,竟然有了起色。根据病情调整方子后,又让她用了两个多月的中药,结果,她居然康复了。因为家里已经被她的病拖累得家徒四壁了,刘杰免去了她一大半的药费。 从刘杰的家人口中,记者还了解到:这些年对那些贫困户和五保户,他看病几乎不收钱。每年春节前,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回家过年时,总会看到他在年底盘账时拿出一沓沓厚厚的未付钱的药单,然后极认真地把那些药单整理一遍,从中挑出十之七八,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烧掉——几乎年年如此。每次他都自言自语:“唉——他们都很穷啊。再说了,账不过年……” 这些年来,虽然别的开诊所的同行早就富得流了油,但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刘杰,开诊所所赚到的钱仅仅能维持老两口的日常开支,即使有点儿盈余,他也拿去买了紧俏药品。 国家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刘杰又把自己的个人诊所换上了“大山呼村卫生所”的牌子,肩负起了为全村父老实行“新农合”的重担。 岁月无言登高向远风风雨雨的行医生涯消耗了刘杰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岁月毫不留情地在他脸上雕琢了一道道沧桑的痕迹;陪伴在身边的老药箱也在妻子不断的缝缝补补中逐渐地老去;但岁月惟一无法改变的是他对患者、对父老乡亲的赤诚之心。 刘杰的老伴说:“他这个人,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2002年冬天他感冒了,自己给自己输了几天的水,别人一叫,他又顶着寒风跑出去看病了。几次下来,感冒严重了,高烧了10天,最后不得已到郑州治疗,已经发展成了肝脓肿,花了两万多元钱,住院住到腊月二十七才勉强回家,差点儿把老命送进去。住院就好好治病呗,他还天天念叨那些病号,吵着要回家。伺候他的俺大儿子和儿媳妇,天天还得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安心养病。” 2005年春天,刘杰老两口被他的大儿子接到郑州检查身体,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本刊执行社长、总编詹洪春先生。之后的一天,两人进行了一席长谈。在谈话中,詹洪春被刘杰老先生大半生致力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沧桑经历深深感动,同时也对他在中医诊疗、中西医结合等方面独到的见解和丰富实用的医疗经验所折服。 2005年10月2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华中医药学会等部门举办的“全国中医药中医名医品牌战略论坛及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詹洪春等人的推荐,刘杰作为来自农村最基层的惟一一位参会人员应邀参加了这次全国中医药学术会议。鉴于他在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刘杰与到会的几十位中医药专家、教授一起,被这次“中医名医品牌大会”授予“全国中医名医”称号,并颁发了奖牌和证书。为了农村父老乡亲的健康事业奔忙了大半辈子的刘杰老先生,终于获得了国家最高学术部门和社会的认可与表彰。 2006年7月底,第七届张子和学术研讨会暨全国中西医医药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刘杰再次受邀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 前不久,河南省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刘宏兆提出的建议国家实行“乡镇医生职业资格(简称乡医)”的设想,经本刊报道后,引起了相关领导及社会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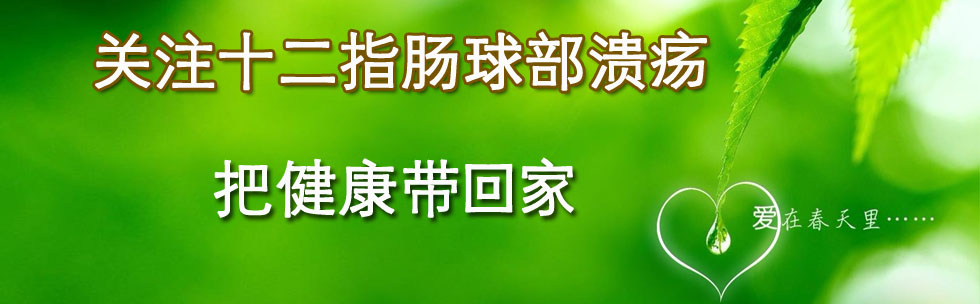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